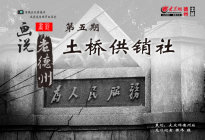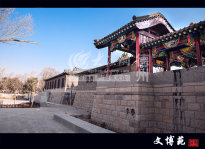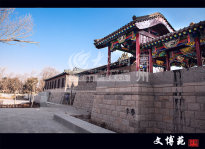王海霞
“带上几个窝头尝尝,我用黑豆、黄豆、玉米、小米面做的,成本比馒头还高!”周末回家,走时,母亲给我带上了一袋她自己蒸的窝头。
过去,母亲一直都痛恨窝头的。那时,一年到头几乎都要吃窝头。母亲怀我临产时,姥姥心疼闺女,把自己省下的白面给她做成了馒头,而母亲又体贴干重活的父亲,把白面馒头全省给了父亲,自己仍旧啃窝头。
“啃了半辈子的窝头,再也不想那东西了。”母亲不止一次给我们姐弟表明她对窝头的态度,而今,窝头却又成了她和父亲餐桌上的常客。
我对窝头没有母亲那样起起伏伏的情感,它唤醒的是我关于童年的快乐记忆。小时,贪玩的我常赖在奶奶家。既可以毫无顾忌地和小伙伴们玩得天昏地暗,不用担心母亲的责骂,又可以吃到奶奶做的窝头。
奶奶比母亲吃过的窝头还要多,但她对窝头有种虔诚的感恩。即使家家户户可以敞开吃白面馒头时,奶奶对窝头的这种感情也没有随着生活的富裕而减少。隔三岔五会蒸上一大锅玉米面窝头,有时还贴黄澄澄的玉米饼子,还用白菜、香菜叶、榆钱叶等蒸菜窝头。天生好胃口的我对所有的窝头都喜欢,这种喜欢颠覆了母亲言论带给我的影响。
记忆中,奶奶做得最好吃的是棒子粥窝头,那几乎是每个冬天一成不变的早餐。当柴火烧的大铁锅沸腾时,奶奶便将捏好的小窝头和玉米面一块下锅煮,基本煮上两个开锅,再小火焖上一会儿便好了。第一次见到这种小窝头时,我惊奇不已,窝头似栗子般大小,完全是大窝头的微缩版。由于粥的浸润,玉米的清香味更浓。做窝头时,奶奶加了盐,吃窝头喝粥,咸淡相宜,我能一口气吃上一大碗,棒子粥窝头的香气温暖了我童年的冬天。
上初中住校了,再也不能经常吃奶奶做的小窝头了,有时实在忍不住馋虫的勾引,赶上放假时,跑去央求奶奶给我解馋。再后来,离家求学、上班、恋爱、结婚,时光的流逝,我已经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小丫头变成了母亲,而奶奶却卧病在床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。每次去看奶奶,听到她因无法说话而发出的呜呜声,心便似刀割般难受。奶奶瘫痪三年,受尽病痛的折磨后,离开了人世,也带走了棒子粥窝头的清香。
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,穷困标志的窝头成了人们追求营养饮食的“新宠”,虽然,现在市场上的窝头品种繁多,但无论是小米面、栗子面、南瓜面,还是其它什么新鲜配料的花样品种,都无法让我吃出棒子粥小窝头的味道。
常常在对棒子粥窝头的怀念里浮现奶奶做小窝头的情景,天堂的奶奶要是知道她喜欢的窝头,今天这么受尊崇,一定会很开心吧!
初审编辑:马宝涛
责任编辑:蔡亚会